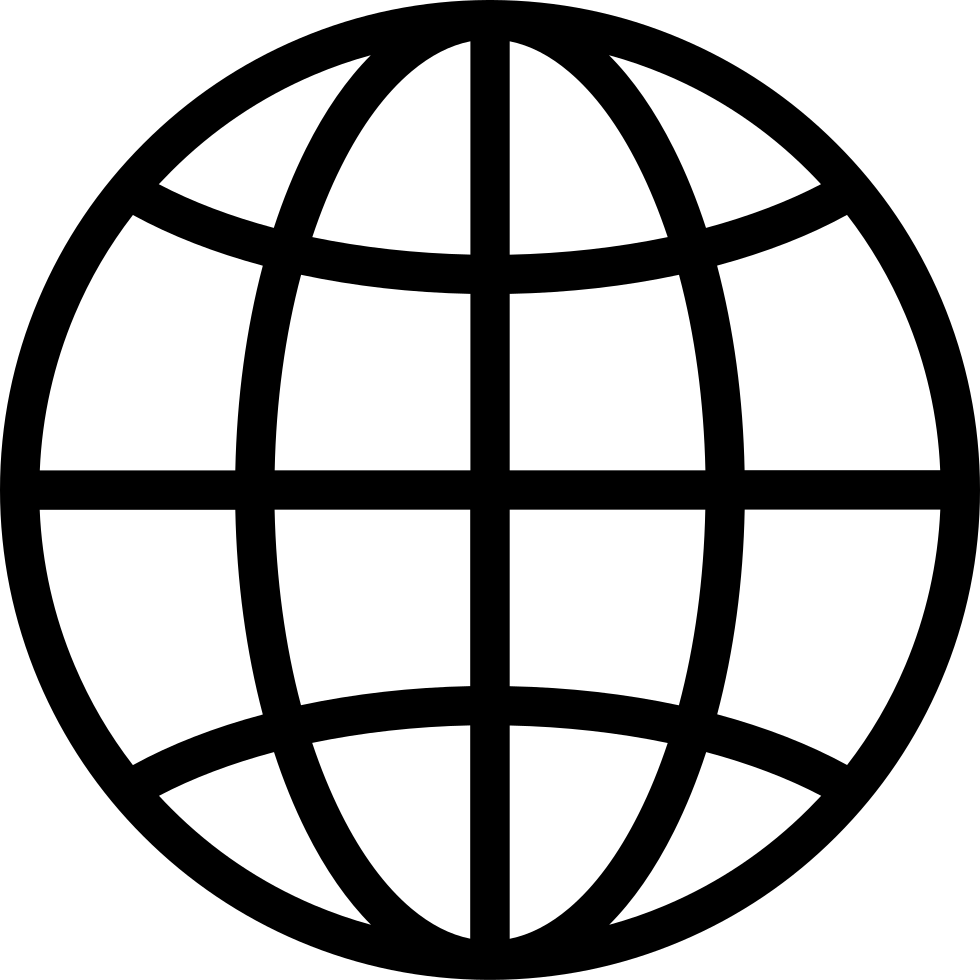白日漫游:北京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Manage episode 329529037 series 1317178

北京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想工作,又害怕失业;想要恋爱,却又恐惧婚姻;有呐喊,更有彷徨;一心要逃离,却不 知逃向何处;从北京、上海到广州、深圳,在所有地方都只能与自己的影子相遇。青年作家远子最新力作,以十四篇彼此独立而又互有呼应的短篇小说,刻画在大都市挣扎求 生的年轻人,描述一种渴望自由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生活状态,记录一场疯狂、残酷而又不 失诗意的心灵之旅。
作者:远子 | 主播:沧蓝 | 制作:郡子
北京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一天也不想留。我算是发现了,一旦生活在北京,你就再也感受不到世界的辽阔,这里的一切都把你紧紧锁在地上。很多时候,你只是想自由自在地做一个不幸的人,可是那些有房有车的人一天到晚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光是一个首付就得我不吃不喝挣几十年工资。关键是他们还要告诉你他们有多痛苦,甚至比你还惨。我真羡慕你不用买房,你可不知道买个房有多难,一个前不久刚买到房的朋友就是这么跟我讲的……我受够了,我想去流浪, 我要去南方。
离开北京的那天是一个大晴天,多么可怕,小心翼翼的蓝里分明带着纵欲的痕迹,又像是在供给我们一种没有勇气去实现的希望。只有在雾霾天里,人们才活出他们该有的样子 :沉重、麻木,而又无所畏惧。我头疼,我并不想抒情。我没有制定计划的习惯,从来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计划只对相信明天的人才有用。我决定先去上海见一个诗人,我的朋友阿立。买票的时候已经只剩下高铁了。高铁开得真快啊,窗外景色消失的速度让我头晕,不过我很喜欢“二等座”这个说法,它提醒我认清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白日漫游
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出来后,阿立的电话却打不通,他说过会来接我,我就没问他的住址。举目无亲的我拖着行李箱在街上四处乱逛,万向轮滑动的声音使我心烦。我跟在一辆行驶缓慢的扫街车后面,盯着那两个不停旋转的车刷看,心想要是它们能把我体内的垃圾都扫走该多好…… 我该去哪里啊?我还是先去找一个住处吧,我的积蓄还不至于让我露宿街头,不过也快了。
小旅馆很便宜,床单有一种肮脏的白,我躺在上面抽烟,听隔壁情侣吵架。他们的方言我听不太懂,像是在唱戏,但不妨碍我认真听了半个小时。不然我还能做什么?看电视吗?活着可真没意思,我又不敢死,问题就这么简单 :我苟且偷生。在通讯录里翻找了一遍住在上海的朋友,我决定问问苏羞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我们之前在网上交流很多,关于文学和电影。是啊,生活在这个国家就这么点好处,做一个文艺青年的成本很低,书很便宜,电影可以免费下载。不过,我接触苏羞的目的只是为了性,她的目的我不得而知。她说来上海一定记得找她,谁知道这是不是客套话……她却很爽快地答应了。
见面的餐馆在巨鹿路,比我想象中高档。我担心我的肩膀上有头皮屑,就趁她还没到,先去了趟洗手间。她穿的衣服很合身,笑的时候,眼睛里好像有酒窝,比照片上好看。我想亲你,吻你,把你抱在怀里,像剥柚子一样脱掉你的衣服,露出你年轻的肉体。我们的眼睛彼此注视, 舌头互相缠绕,身上凹凸的部分正好砌成一道墙,就让我们躲在墙里整日整夜自言自语吧,难道这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人忘却肉体的办法?当然我不能说出我的心声。我甚至不时提醒自己挺直腰板,以便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尽管我不知道我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苏羞问我来上海做什么,我说来出差,事实上我已经失业很久了。我问苏羞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她说在经营一家网店。我问是不是能挣很多钱,她说不多但能糊口。我问她最近在看什么书,她说她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没什么可聊的了,我想回旅馆。
我真后悔抢着买了单,这么难吃的菜居然要这么贵, 我离破产又近了一步。吃完饭才八点,她提议去附近的公园走走。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信号,我欣然应约。全国上下的公园都差不多,一堆健身器材,一片胡须般的小树林和一群饱食终日的散步者。这些人到底都吃了些什么,需要费这么大力气来消食?还有那些在雾霾天跑步的人,究竟图些什么?我总是喜欢走神,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苏羞身上才对。白天的空气热得像被煮过,有一层看不见的棉絮裹在我们身上。现在气温降下来了,夜晚露出了它美丽的内脏,我们坐在长椅上,身后有柳树。

“柳树真好啊,它们的叶子那么温柔地滑过你的脸。即使你在奔跑的时候不小心撞上,它们也不会反击你。”
苏羞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因为正常人通常不会这么讲话,而我讨厌正常人,所以我得避开工作,格子间里盛产正常人。
“你不觉得它也有很可怕的一面吗?”我这个人天生爱唱反调,“那些柳条披头散发地垂在半空中,像是要控诉什么,却又一言不发。刮风时又完全失去理智,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
“那是风的错,能怪树吗?”苏羞说,“你心里有什么,看见的就是什么。”
好吧,你说的都对,十点了,我只想知道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个公园里至少有一百万只蚊子,我感觉我快要被它们咬到贫血了,我们只能来回走动,但我走不动了,我困了,我头疼。我试着拥抱她,抚摸她的后背, 她没有反抗。她说时间不早了,她该回家了。我提议送她回去。她说好……没想到这么顺利。现在的问题是,她家里有避孕套吗?来的路上,我怎么没想到要买一个呢?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中年妇女,戴着一副上个世纪的金丝眼镜。她问我们有没有看最近的一部热播剧,苏羞在看, 她们便热烈地讨论起了剧情。我只好凝视窗外的不夜城。那些发光的建筑物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营,睥睨着注视它们的人。东方明珠真丑啊,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的地标性建筑真是可怜。据说莫泊桑经常去埃菲尔铁塔下面的咖啡馆喝咖啡,别人问他你之前不是一直反对修建铁塔吗,他说是啊,谁叫这是整个巴黎唯一看不见这个丑东西的地方呢。
也许我明天也应该去东方明珠上吃个饭,我记得那上面有一家旋转餐厅。我应该花完身上所有的钱,然后从那上面跳下去。
小区的保安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他翘起的嘴角里藏着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阴险。他以为他在捍卫道德,却没有意识到人类历史上所有试图使人们变得道德的手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道德的。还好我只是一个过客,这些陌生人还没有想到伤害我的办法……我又开始神游了,想这些没用的做什么呢?我应该找一个借口去买避孕套,可我却稀里糊涂跟着苏羞上了楼。
她家的房子真大,从卫生间里出来我都快要迷路了。苏羞坐在阳台的小圆桌边倒酒,她脱掉黑色丝袜顺手塞进裤袋里,这个动作令我心动不已。路过客厅时,我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婚纱照。原来苏羞已经结婚了,那个老男人一定很有钱,这是很简单的推理。她既然不说,我也不会问。她家住在苏州河边。苏州河这个名字多美啊,苏州河不在苏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的诗意。但是腥臭味从河上飘了过来,那些河水就像是周围的建筑物在白天流下的汗水。高楼把它们肋骨的阴影投到水面上,像孤独的海怪。
“你看这座城市像不像一座图书馆,每幢楼都是一本书,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脚注。”苏羞的抒情让我想哭。
“那我就是一根不小心落入书中的头发,从来都不属于哪本书。”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到河对岸的房子里有人轻轻拉上了窗帘,可我的视力不可能那么好。难道我已经喝醉了吗?我不该喝那么多。
她家阳台上种着洋红色的三角梅,鲜艳得有些失真。我问她那是不是真花,她笑而不语。她和我想的是同一件事吗?她说她想睡觉了,我跟着她走到卧室,她却把我扶到了次卧,笑着说我们还是分开睡吧。我以为她这是半推半就,就把她摁倒在床上,结果她给了我一巴掌。她说对不起,我心情不好,压力很大,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上个月去医院,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我已经没有性欲了。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药,向我证明她确实有病。一只丝袜掉了出来,但她没有发现。我正想说点什么,她却哭了。我最怕女人的眼泪,真的,她们那些泛光的液体像是一种魔咒,我毫无还手之力,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对女人的眼泪无动于衷。多年前有个我不喜欢的女生向我表白,被我拒绝后,她大哭了一场。我不知道怎么制止这哭声,只好答应了她,结果我们交往了三年。我的不幸是无力拒绝他人的不幸,太宰治的这句话简直就是我的心里独白。总之,我慌忙从客厅取来纸巾给苏羞擦泪,又扶她回到主卧,就差唱儿歌哄她睡觉了。
次卧是她网店的仓库,堆满了各种款式的衣服。她养的黑猫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躲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一口吃掉。上海的夜晚好像比北京更亮, 我躺在床上抽烟,睡不着觉。我以前读过一篇小说,忘了是谁写的,说是有一个四处流浪的人,每到一处都要自慰一次,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去过这个地方。我被这个想法折磨了很多年,在不少城市都这么干过,我捡起苏羞用过的纸巾准备再干一次,可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头疼得厉害,只好中途作罢。
我又掏出手机找人,也许可以问问老秦。他是我在北京饭局上认识的一个画家,去年才来的上海。那天他喝多了,散席后大家一哄而散,我便把他带到了我的住处,一路上他都靠在我肩膀上,他的头可真沉,可能因为里面装了太多的思想。我那张单人床非常小,靠墙还摆了一排书, 我们几乎是叠罗汉一般睡了一夜。半夜他还吐到我的书上,毁掉我好几本昆德拉。不过在这之后,有什么蹭吃蹭喝的饭局,他都会叫上我。就我所知,他的画就像我的小说一样根本无人问津,不过从社交平台上更新的状态来看,他最近好像过得还不错。我运气还行,老秦还没睡,给我发了地址,让我现在就过去找他。外面好像有点冷了,我担心着凉,就从苏羞的库存里抽出一件条纹衬衫套在身上, 又顺手捡起她遗落的丝袜,出了门。老秦住的地方离这里不算太远,我决定走过去。街道又重新向我开放了,其实城市里的街道还是不错的,至少它接纳所有的流浪汉。走在上面的人就有点无情了,都这么晚了,大家还是走得那么快,那么互不相干。

老秦看上去很憔悴,给我开门的动作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调整自己的棺材盖。他住在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隔间里,地板上铺满了报纸,上面东一块西一块泼溅着颜料,颇有点波洛克的意思,也许这也是他的作品?他用白布把画架上的画给盖住了,看不出他在画些什么。我其实并不想知道,但还是假装好奇地问他。“我在画我的噩梦,你看了会害怕的。”他给我开了一瓶冰啤酒,第一口啤酒的滋味是最好的。我正想着该怎么接话,老秦忽然劈头盖脸地问我,你知道吗?我们的好日子不多了。我说,我们有过好日子吗?他说以后的日子会更糟,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说做点什么?他说,也许我们该先学着啃树皮,你得知道哪种树皮最好吃,哪种树皮最适宜保存。说完他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铁盒,他说这是栾树、银杏和法国梧桐的树皮,是他这几天在小区附近收集的,问我要不要试试看。老秦疯了。被我拒绝后,他收起铁盒开始抽烟,我也抽烟,我们坐在床上欣赏烟雾。
老秦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说像我这种只住得起地下室的人,与其等着被驱逐,还不如提前离开,这样多少也能保留一点尊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艺术家就应该保持这种愤怒。我问他租的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他说不要钱,是他一个朋友的房子,那个女人是一个成功人士,这两年创业挣了不少钱。老秦居然被包养了,这是我毕生的梦想啊,可是老秦觉得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心里有愧,所以决定只住储物间,剩下的房子都空着。老秦真的疯了。我想听听他和那个女人交往的故事,也许能从中学到一点经验。可是老秦说他困了,能不能明天早上起来再聊。我掏出手机,脱掉牛仔裤准备睡觉,苏羞的丝袜露了出来。看到丝袜,老秦两眼放光,他说操,没想到你还好这口,走,我们去找密斯吧,也不枉你来上海走一遭。我说好。
我们来到小区门口亮着红灯的足疗店,却发现还需要排队,三个躁动不安的男人坐在沙发上抽烟,其中有一个人长着一张像是用腊肉拼成的脸。前台小姐说,很抱歉,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生意特别好,再等几分钟,很快就会有空房间。老秦等不及,那三个雄性动物敌视的目光也让我很不舒服,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去下一个地点。老秦说他知道一个会所,里面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复制品,是波提切利《春》,他最喜欢的是像冬天的大地般赤裸着身体、嘴里冒出花朵的克洛里斯,每次去都流连忘返。老秦专业的艺术赏析把我说得心潮澎湃,我今晚被苏羞激起的情欲总算也能找到一个出口。
实际情形却相距甚远,接待我的阿格莱亚与其说是壮丽,不如说是粗壮。我说美惠女神不是有仨,能不能换一个。她说欢乐女神回老家奔丧了,激励女神正忙。不要换人了,她今晚还没开张。真是该死,我的同情心太泛滥了,我居然点了点头。她一边给我按摩,一边跟我闲聊。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她便问我有没有去过主席纪念堂。看我一言不发,她就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她说她以前在长沙做公共汽车售票员,有一个小儿子,本来日子过得挺舒坦,谁知老公有了外遇,她到老公单位去闹,害他丢了工作。他们就离了婚,孩子判给她。一个人养孩子压力大,只好出来做……没完没了的,我他妈根本就不想听, 我想吐,我头疼。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老秦在门外大喊, 便急忙穿好衣服冲了出去,只见老秦正和保安纠缠在一块。上回还可以,这回为什么不行?老秦认死理。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保安冲他大吼。我急忙付完钱,搀扶老秦走了出来。
老秦很生气,又不甘心,于是带着我去沪太路,说客运站那边有一幅《土耳其浴室》,那一个个啊,可是楚楚动人、天生媚骨……我不再轻信他的成语,果然,到了之后我们走了好几条弄堂,连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和我们一样形迹可疑的男人。我说要不回去睡觉吧。老秦更不甘心了,说上个月他还来过,这会儿怎么就没了。
阿立忽然给我打电话了,说他现在在外滩。我问老秦去不去,他说去,他得给这个夜晚寻找一个句号,不能全是逗号。阿立靠在黄浦江边的栏杆上喝闷酒。他夸我的衬衫不错,很洋气,我就给他讲了这件衣服的来历。他说他今晚的遭遇比我更离奇。原来他是要去火车站接我的,结果在地铁上偶遇了来上海出差的初恋女友,他便陪她一起去酒店放好行李,一起吃了晚饭,喝了咖啡,还陪她去了福建中路上的译文出版社,因为她喜欢村上春树——当年还是阿立推荐她看的。他给她拍了好多照片,拍着拍着, 竟忘了他们早已是对方的过去,隔了好一会才恍过神来。

他不停向她提起十年前的上海之行。那时他们才二十岁,刚上大学,暑假期间来上海见一个共同的好友。他们三人来到东方明珠,却没钱上去,就在塔下拍了一张标准的游客照。照片拍得很好,洋溢着青春气息。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那张照片,直到听说她嫁给了那个好友。他并没有怪她,因为是他提的分手,他当时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 难免有了雅俗之分。他觉得自己的女友很庸俗,连里尔克、策兰和 T.S. 艾略特都不知道是谁,后来他才意识到那些成天把大师挂在嘴上的诗人其实都是蠢货,所以他很后悔,可是一切都晚了。
他同她聊天,观察她的反应,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点破绽,以便钻进去重温旧情。比起按部就班的恋情,他更欣赏这种重逢的戏剧性。她向他讲起高中时的班主任、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聊了一会新上任的美国总统, 可就是对他们之前的感情闭口不谈,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他觉得是方言限制了他们感情的表达,于是改说普通话。可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她讲话的语气依然没有改变, 始终带着一种冰冷的客气。他又不能当着她的面念诗…… 最后他只好向她道声晚安,独自一人回到住处。
阿立的故事让我们很伤感,我和老秦都想安慰他几句,就举起啤酒瓶说了句 :“干。”可阿立说,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高潮。他站在返程的地铁上,头晕目眩,像是做了一场悲伤的梦。他这一天说了太多的话,耗氧量太大,胸口很难受,仿佛有人在拿细密的针头刺他的心脏。他决定闭目养神,结果等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原来他已经晕倒了。阿立说晕倒的感觉太爽了,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就像是经历了一次小型的无痛死亡,死神通过眩晕友好地拜访人类。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整个过程中都有人在诚心诚意地帮他。先是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掐他人中,在他鼻子下面抹上清凉油,唤醒了他 ;到站后,地铁保安把他扶下车, 叫了急救车 ;有个路过的小姑娘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 问他吃不吃,说是刚洗过的。“这世上还是有真情的,我们把这个社会想象得太过残酷了,没有那么多敌人,也没有那么多地狱。”阿立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不要再钻牛角尖了,不要再死死抱住那点可怜的自我不放。”
阿立塞林格式的总结发言并不能说服我,甚至让我有些厌烦,我看到老秦也笑着摇了摇头。一心想要让自己心里舒服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过我不想打击阿立,也害怕吵架,光是与自己争论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我比较关心他上救护车之后的事,就我所知他是付不起医疗费的。他说上车之后他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就骗医护人员说自己想上厕所。车还没停稳,他就跳下车跑掉了。他跑回家躺在床上,为自己得出如此正面的结论而激动不已。他睡不着觉,就又跑到江边来吹风,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我。
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已经是凌晨四点了,东方明珠早已熄灭,江边却还是有几个游客在拍照和尖叫。和这些愉快的人相比,我们仨就像是飘在牛奶上的苍蝇。到处都是愚蠢的和平景象,我感到恶心。一个人似乎只有把自己严格限定在动物的范畴内生活才能避免痛苦,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在人类和动物之间做出区分?我都开始自我拷问了, 看来这下我真的喝醉了,我已经感觉不到头疼了。我失去了身体的所有权,只剩下部分使用权。我把身体重心交给栏杆,掏出口袋里的最后一根烟点上,顺手把苏羞的丝袜扔进了黄浦江,它像一只黑色水母缓缓游向彼岸。一个清洁工正拿着高压喷头清洗观景平台,那道喷涌而出的水柱看上去力大无比,足以抹除所有历史痕迹。如果留在原地不动的话,我敢肯定我们也会像垃圾一样被冲走……


824 episodes